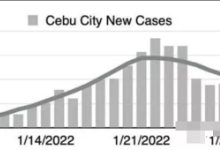菠菜与赌博相比而言,究竟不同在哪几个地方!
人类的赌博行为,可以简单到孩子们玩的“包、剪、揼”,也可以复杂至需要电脑模拟。
澳大利亚菠菜学者麦克费尔森(John Mcpherson)在其所编著的、迄今所见最详细的菠菜辞典《Beating the Odds》中,给“赌博”(Gamble)一词分别下了三个定义:一、以任何方式对注码展开的竞争;二、用钱或任何有价物对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最终结果进行冒险;三、在一个碰运气的游戏中,用钱或其他有价物进行冒险。
研究狭义菠菜经济学
另一本更为流行但更为简要的菠菜辞典《Casino Gaming Dictionary》(George Fenich & Kathryn Hashimoto着),给“赌博”下的定义是:对一个不确定的结果作出预测判断,并以所押上的钱来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从以上两家四个定义中,可以浓缩出赌博的四要素:下注、竞争、冒险、不确定性或碰运气。
澳门的菠菜法律中对“幸运菠菜”的定义是:结果为不确定而菠菜者纯粹或主要是靠运气之菠菜。这一定义是对上述四要素中之最后一个要素“不确定性”的强调,即纯粹或主要是靠运气。这一点对于理解赌博的概念其实很关键。
我们不妨把上述这些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归纳一下。从广义上说,人们在面对任何不确定性而采取行动时,皆是一种赌博;赌博因而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赌博者是在与自己的命运对赌,而不一定是在与他人对赌。鲁宾逊在荒岛上独自一人,也可以赌博。当他深入荒岛寻找水源时,他押的赌注是:不会遇到猛兽被吃掉,不会迷路而渴死。如果赌输了,他是输给了自己的坏运气,而不是输给了他人。广义的赌博,不一定是社会行为。
狭义的赌博定义是:赌博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靠运气以决胜负的竞争方式,是人类诸多决胜负的竞争方式中的一种。狭义的赌博中,输者之所输乃赢者之所赢。从这个意义上说,赌博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社会分配的机制。
赌场中的赌博,显然属于狭义的赌博。菠菜经济学,研究的是狭义的赌博行为。
易染赌瘾因全靠运气
本文将与赌场有关的赌博行为进一步定义如下:
赌场中之赌博,是赌博者以碰运气的方式、通过风险对抗而相互谋取对方钱财的行为。
判定一种游戏是否赌博,主要依据的是两个因素:(一)有赌注;(二)输赢决于运气。二者缺一,不成其赌博。举例说明:阿猫与阿狗两人摔跤,讲好败者输给胜者一万块钱。他们确实在赌钱,但不是靠运气,而是凭力气。在这个例子中,赌博的第一要素具备了,但不具备第二要素,因而不能算赌博。
内地曾有一段时间盛行打扑克,满街都是扑克摊,都是“干玩儿”的,最多输者脸上贴块纸。打扑克,胜负主要决于抓到牌好坏,故而符合“主要是靠运气”的第二要素。但因为是“干玩儿”,没有赌注,故不具备上述第一要素,不能算赌博。
还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是:赌博容易上瘾的原因,不是因为第一要素,不是因为极易让人眼红的东西——钱,而是因为赌博的第二构成要素——输赢决于运气。通过摔跤或下棋赌钱,一般不会使人上瘾。而那种“一翻两瞪眼”的游戏,则极易将赌徒的幸运幻觉勾引出来,并使之在这种幻觉中丧失理智。
自从人们为赌博找了一个学名“菠菜”以后,再说到赌博时,人们就更愿意使用它的学名了;就如自从人们为“厕所”找了一个更好听的学名“洗手间”以后,人们就更愿意用后者了。
一意两词易制造麻烦
然而,这个好听不好听之别,后来开始反过来影响这两个词的词义,并使二者开始发生分离。由于赌博一词比菠菜难听,故而近年来,中国人在说到非法赌博时,更愿意使用“赌博”一词,而在说到合法赌博(如内地的合法彩票和澳门的赌场)时,则更多地使用菠菜一词。渐渐地,约定俗成,赌博一词的非法色彩越来越浓,而菠菜一词也越来越成为合法赌博的代名词了。本来由经济学将之定义为同义词的“赌博”与“菠菜”,受到了伦理学和法律学的“污染”,闹得经济学恐怕最后也不得不入乡随俗,接受这一污染结果,承认菠菜与赌博的分裂。人类的语言就是这样演化的。
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一样,台湾人也认为“赌博”这个词不好听,也给它找了一个学名,不过不叫“菠菜”,而是叫“博弈”。然而,博弈是汉语中原来就有的一个词,并有着明确的含义,就是“下棋”。现在,要让这同一个词“戴两顶帽”,让它兼有下棋和赌博的意思,这可有点麻烦,或者说,这将会制造麻烦。类似的先例有:中国人初学西医的时候,不知道LIVER这个词怎么翻译,为了图省事,便从中医中把“肝”这个词拿了过来;不知道KIDNEY怎么翻译,便把中医中的“肾”拿了过来;等等。如此翻译,给后世的中医与西医,不知道制造了多少混乱和麻烦。
笔者倒是觉得:赌博就是赌博,何必美其名之菠菜或博弈?直呼其名,又有何妨?





 本文采纳自社区会员"
本文采纳自社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