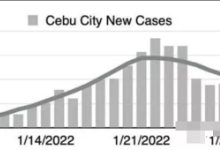“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 (东西问)季芳桐:“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作者 季芳桐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清至民国初期,中国穆斯林先贤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史称“伊儒会通”。作为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伊儒会通”有何特点?对当下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又有何启示?
何谓“伊儒会通”?
作为历史事件,“伊儒会通”具体指发生于明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期的中国穆斯林先贤的文化自觉活动,以译撰为特征,通过对伊斯兰教著作的汉语翻译,将外来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活动,为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或者说走出了一条道路。“伊儒会通”既是过去的一段历史,也可视为当下乃至将来工作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场历史的文化自觉活动,身处金陵(南京)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是“伊儒会通”的开拓者,其出版了第一部汉文的伊斯兰教著作《正教真诠》等,率先将伊儒文化进行了会通;而身处云南的马注、马德新等则是活动的推动者,其著作《清真指南》《大化总归》等大大推进了“伊儒会通”的广度和深度;而同处金陵的刘智及其著作《天方性理》则是“伊儒会通”活动成就最高代表。
这批穆斯林学者在一生中都有或学习或探讨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经典的经历。例如:刘智自述阅读儒教之经史子集八年、伊斯兰教著作六年、佛教典籍三年、道教经典一年及阅读137种西洋书籍。王岱舆虽然阅读时间、顺序略有差异,但是四教(伊、儒、道、佛)的著作也都阅读研讨过,被称为“学贯四教”的人物。学术经历与学术成果是两个方面,但成果也能够证明他们的会通往往是四教而非仅仅两教之会通。王岱舆的三部著作,以及刘智的代表作里都可以发现四教会通的观点与成果。
可以说,“伊儒会通”从字面看是指伊儒两教的会通,而实质包括四教的会通,涉及领域首先是伊斯兰教教义与儒教教义的会通,其次是伊斯兰教的苏菲功修与道教、佛教的修持会通;再者是伊斯兰教的教律、教规与儒教礼法的会通。换言之,会通活动主要在这三个领域进行,成果也多聚集在这些领域。当然,这次活动持续了三百年左右,而这批人物成果很多,难以一言尽之。最大成果就是构建了汉语的伊斯兰教体系,其中既有体系框架,又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等,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会通”后还是伊斯兰教吗?
不同文化间的会通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放眼望去,无论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概莫能外。而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会通才能够发展得更好,才能够将文化发展推向新的高峰。这是世界文化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和趋势。
伊斯兰教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虽发源于阿拉伯,必将走向世界,也必然会与东方的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进行会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有人担心一旦“会通”了,还是伊斯兰教吗?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以伊朗的波斯文化为例,当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会通后,形成的波斯伊斯兰文化不也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吗?在历史上未曾有人对“伊波会通”感到忧虑,为何与中国文化会通就感到忧虑呢?
“伊儒会通”作为一场历史的活动是有始终的,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期,有持久性或永恒性。如人所知,“伊儒会通”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新中国建立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伊儒会通”的理论在全国传播、普及,只是各地的中国化发展并不平衡。例如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是维吾尔语,所以对于汉语系统的“伊儒会通”思想成果接触较少,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较其他地区略微慢些。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应该在新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使其更深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加快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当然,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学习、吸收“伊儒会通”的成果是选项之一,不是唯一。换言之,也不排斥其他有利于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方案。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伊儒会通”成果既包含伊斯兰教的根本内容,也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在教义、功修、教规方面一概如此,进而加快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目前伊斯兰教界正在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体系建设。实际上,伊斯兰教经学体系建设不能平地起高楼,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只能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于是,就需要继承“伊儒会通”的理论成果,或者在其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构建和完善,并尽量吸收借鉴国际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优秀成果。“伊儒会通”理论对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其不仅是过去式,更是现在式、乃至将来式。
“伊儒会通”对东西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伊儒会通”的经验对于东西文明互鉴亦有一定启示。“伊儒会通”主要是相互吸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其中也包括相互批评、相互争鸣。若是一味地颂扬,只见其长不见其短,也不利于学术发展。于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对于儒教、佛教、道教的某些观点的批评,例如儒教传统习俗以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岱舆指出,孝敬不孝敬是伦理问题,是否有子嗣是生理问题,把生理问题归为伦理问题是犯了逻辑错误。应该说,这个评批非常到位,也非常准确。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生活的儒道佛学者却没有发现或者不曾指出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思维定式使然,没有进行思考或辨析已经存在的传统观念。一旦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鉴,有了不同意见或批评,对于儒教的完善当然有积极意义。这个经验对于东西文明互鉴也应适用。东西文明当然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或者说,是以学习、借鉴为主,也不排斥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不足,才能促进各自反省,才能够促进各自发展,最终达到互鉴的目的。
从微观角度看,东西文明互鉴离不开著作的翻译,尤其是经典的翻译。“伊儒会通”的代表人物多是学通四教的人物,而四教中有三教(儒、道、佛)属于中华传统的文化。换言之,他们都具备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实功底然后才进行翻译和会通的,于是获得了好的效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人以为只要熟悉西文经典,将其翻译过来即可,而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积累,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自然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其结果不仅西方文明的精髓没传播进来,而且译文也读不懂乃至不知所云。更有甚者,不少经典的再译远不及原译,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熟悉中华传统文明。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文明互鉴工作首先是要系统学习并熟悉东西两种文明,而绝非一种文明;作为一位中国人你若不熟悉东方文明,自然也就不可能熟悉西方文明,如此一来,何论互鉴?(完)
季芳桐,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南京理工大学沙特研究中心首席教授,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儒思想会通研究”主持人。